9月26日,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北学研究院与雄安新区宣传中心联合主办的“北学·容城三贤学术研讨会”在雄安容城召开。河北省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省社科联第一副主席康振海出席开幕式并讲话,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陈峰致辞,省社科院一级巡视员杨思远主持开幕式,容城县委副书记任桓致欢迎辞,学者代表九州·体育国学院院长张京华教授发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北学”和“容城三贤”开展学术交流研讨。会议期间,与会学者拜谒了杨继盛祠堂和孙奇逢纪念馆。

张京华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学派还是道统——从〈理学宗传〉到〈北编〉》的论文并作发言。会议期间,张京华教授参加了“儒学如何走入和影响时代”的学术对话。此外,张京华教授还接受了超星凯旋影视传媒公司以及容城地方媒体的两次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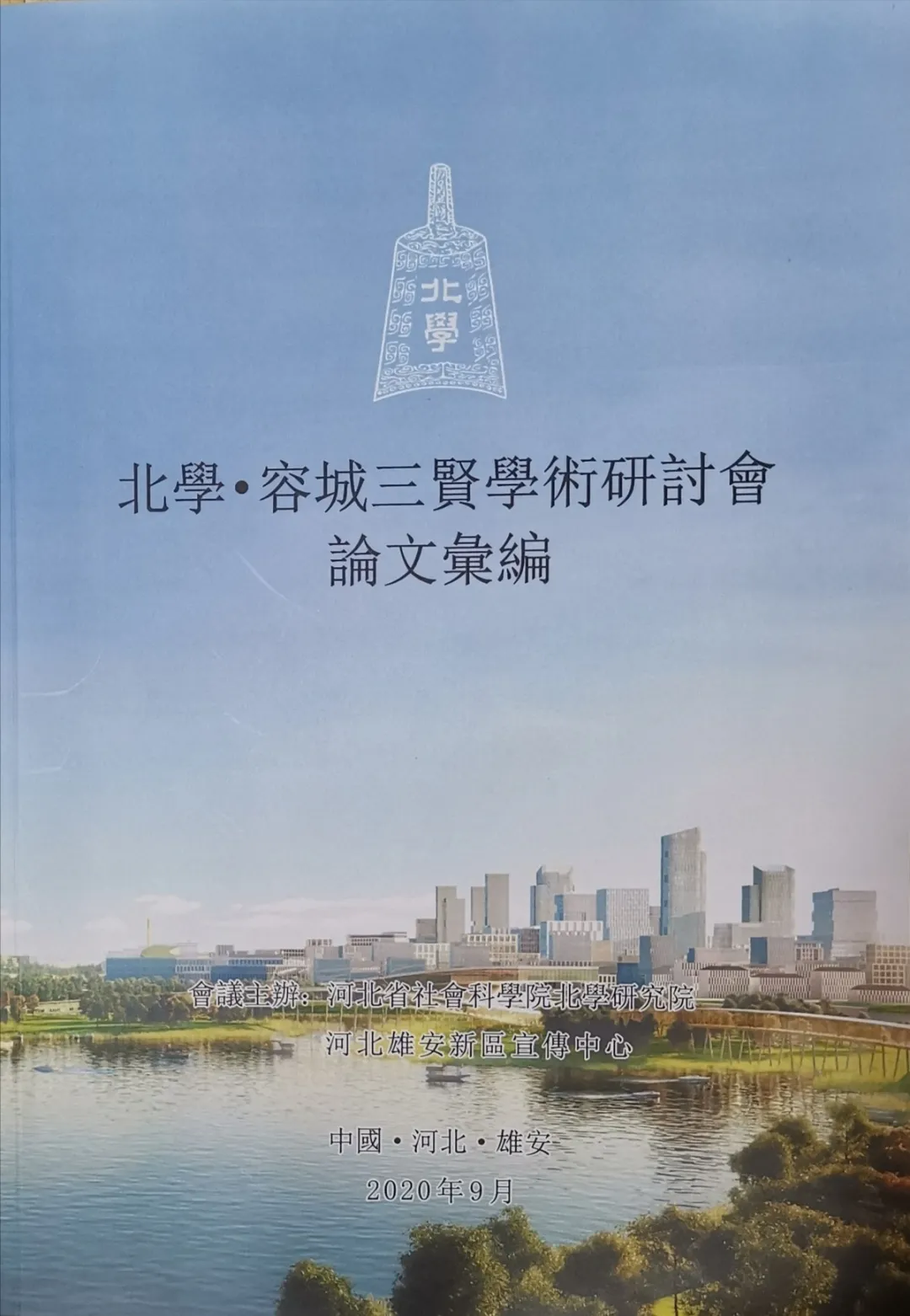
张京华教授在“北学•容城三贤”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的书面发言说:
今天能叨陪前辈,侧席“北学·容城三贤”学术研讨会,感到十分荣幸。最近河北学界成立北学研究院,编纂《北学研究》辑刊,这是学界期待已久的大事,借此机会表示真诚祝愿。
容城人、容城三贤之一孙奇逢,学者尊称夏峰先生,是北学的不祧之祖。康熙十二年(1673),夏峰先生指示自己的两位弟子,魏一鰲编纂《北学编》,汤斌编纂《洛学编》,标志着北学走向新的隆盛。
北学是儒学的一个地域性的支派,夏峰先生自己编纂了《理学宗传》,表明了他承接周程张朱理学道统的立场。同时,夏峰先生又为张沐《道一录》作序。儒学追求绝对真理,天经地义,纲常名教,宇宙原理,清醒理性,天下一体,万物平衡。儒学追求道,追求理,所以两宋儒家又自称儒学为道学、理学。天下的道理只有一个,换言之,道理是天下的必由之路,“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但是,夏峰门派又高张北学的旗帜,这是因为,儒学源远流长,儒学在不同的地域确有不同的侧重。
《中庸》子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唐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北学作为北方的儒学分支,具有不同于其他各地儒学的特质。


北学的特点是经世致用,躬行实践。其思想渊源主要是《书经》《左传》所言“六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
北学在明清之际最盛。就我所知,明清之际北学组织了全国最早的抗清义军,孙奇逢、马鲁、王延善共同起兵,收复容城、雄县、新城三县。
以夏峰先生为中轴,北学渊源上溯到汉儒董仲舒、韩婴、毛苌。中间颜李。下及民国时期,北方有四存学会,编纂《四存月刊》,出版《颜李丛书》,建立四存中学。自古及今,北学源远流长,名家辈出,著述如林,影响巨大。可惜因为实践性的研究,难度高于思想性的研究,所以长期难以展开。今天北学研究院的创建和北学研讨会的召开,可谓适得其时。
清初一些北学家南迁,夏峰先生到了辉县,五公山人王余佑到了献县。已故张岱年先生是献县人,曾请为《五公山人集》题签。
梁世和教授指出:“北学是燕赵文化之体。”《北学研究》征稿启事说:“北学既是燕赵文化的精华,又是北方文化精神的象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本人完全同意这一论断。本人在1995年出版《燕赵文化》,之后一路南下,“日暮途远,倒行逆施”,从北学故地,历经二程故里,上溯濂溪故里。但是本人生是燕赵之人,死是燕赵之鬼,今后河北学界但凡有召唤,北学研究院、梁世和先生但凡有召唤,都甘愿奔命效力。
张京华教授在“北学·容城三贤”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说:(录音整理崔娜)
我参会的小文在会议材料集第248页,谈了谈孙奇逢孙夏峰先生和他门人一起编《理学宗传》和《北学编》的事。我跟大家汇报一下这篇文章写作背后我的一个想法。1995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的社长俞晓群组织了一套地域文化丛书,到1998年出版了24个品种,这差不多是当年那个时段上地域文化划分最细、系统最全的一套地域文化丛书。这套地域文化丛书里面,我就被他们指定写燕赵文化的内容,因为之前我有写燕赵历史变迁的想法,后来他们知道这个想法,就把我推荐去写这个小书。

写这个小书过程中我比较注意、比较喜欢的一个人叫做王余佑,所以关于王余佑这一部分我写得比较多,王余佑就是夏峰先生的弟子,王余佑自己的弟子有三个人:一个是颜元,一个是李塨,还有一个是王源。“颜李学派”中颜、李二人都是王余佑的弟子,王源则是清初和魏禧魏冰叔齐名的一个人。王余佑还有个女婿就是魏一鳌魏莲陆,魏莲陆也和王余佑一起做夏峰先生的弟子,就是撰《北学编》的这个人。这些人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主要研究王余佑,但别的人我也都看了看。特别是我到了湖南以后,因为我写了《燕赵文化》,所以王余佑的后裔找到我,给我看了他们家族留下来的,实际上是王余佑创编的他们王氏的家谱,里面有很多他们师门之间的材料,除了齿录之外还附了好多的传记,所以我看到了很多未知的材料。后来我就把王余佑的集子整理出来,早先是《五公山人集》,后来是《王余佑集》,放在《燕赵文库》里了。在做这个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体会,北学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这些人都是明后期从小兴州来的。小兴州当时是一个军事设置,就是一些守边的军人住在那儿,那么军人当然也有家属,这些军镇子弟世世代代生活下来,后来又内迁到河北北部这一带。王余佑是从小兴州来的,孙夏峰、鹿善继也是从小兴州来的,颜元也是从小兴州来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所以他们关系就比较好,相互之间建立着联系。当时这些人有一种为国家效忠的这样一连串的活动、一连串的事迹。那么这些人他们当然都是儒家的,古代只要稍微杰出一点儿的人物都会读书,读书就都是儒家,而这些人的突出之处是懂兵法,甚至懂武术。王余佑有一部讲战略的兵法书《乾坤大略》,他还有一部武术书叫做《太极连环刀法》。他会武术,可以骑马射箭,他跟颜元、李塨在一块练武,他们这些人就是这样。今天上午有学者讲到中国人的弃武从文,文越来越重,武越来越轻,但是在北学传统中,武还是比较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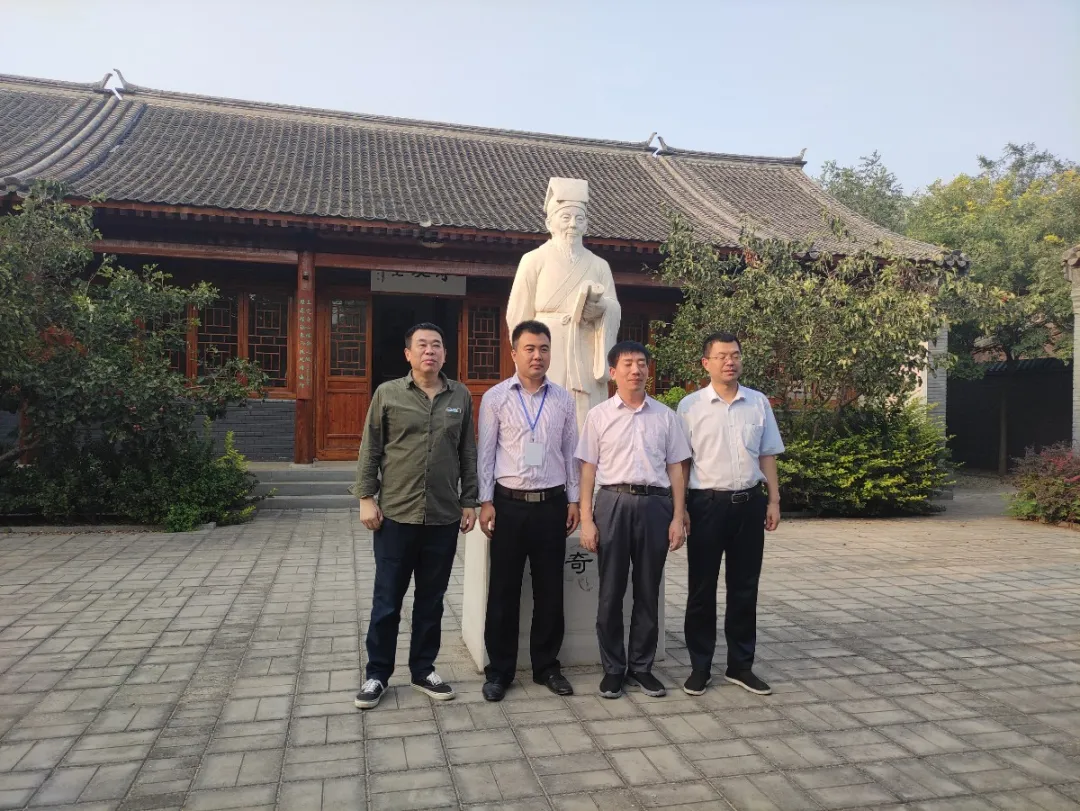
他们在明末做了几件事:
一个就是帮助兵部尚书孙承宗守长城,和茅元仪一起筹划军事,孙承宗著《车营百八叩》的时候,王余佑也是参与者之一。
再往后,阉党就出来了,魏大中、杨涟、左光斗他们就被抓起来了,鹿善继、孙奇逢、张果中、王余佑这些人当时都是平民布衣的身份,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们,都是可歌可泣的。
然后是李自成从陕西出来,他们又防御李自成,多尔衮的八旗军队入关,他们又反抗多尔衮。
再往后他们还收复了河北的三个县城。收复以后守不住,他们就隐居在易县的双峰山,就像《桃花源记》以坞堡为原型那样守起来,变家丁为军队。双峰山上现在还留着书院的遗址。
再往后,清朝的江山稳定了,他们恢复明朝的大业没有希望了,他们就解散,各自回家,这个阶段就有点儿像孔孟的晚年,所谓退而著书、退而修《诗》《书》《礼》《乐》,开始著书立说,在书院讲学,招收弟子,开始传自己的学统,特别是颜元、李塨,都有大部头的哲学著作。
孙奇逢也就是在晚年这个时候开始编撰《北学编》、《洛学编》,开始疏理系统的学术脉络,写了《理学宗传》。《理学宗传》这部书,顾名思义,它一定是认同理学、服膺理学的,他并且把自己当成是理学的传承人物,甚至是暗示自己是理学的正宗传人。所以从学派上看,我觉得要是硬去对比今天的学科划分的话,北学应该算是哲学里边、儒学里边、理学里边的一个专题,算是哲学系、哲学研究所里面的一个研究领域。不过在《北学编》中,编者在表达自己的儒学立场时追溯得比较远,比如说从西汉董子董仲舒追溯下来,董仲舒那时候当然没有“北学”这个名称,但是他把它追溯到这儿,做的是一种广义的扩充。在这种广义的扩充里面,“北学”的概念就非常宽。稍晚的时候河北这一带有《畿辅丛书》,到《北学编》的续编、补编就参照了《畿辅丛书》,把《畿辅丛书》里收录的有著作的学者、比较不错的人物都收进来,就是河北的文化名人都收进来,那么《北学编》也是这个倾向,就是河北历代文化名人,远古的先贤、僻居的乡贤都收进来,所以其实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北学”就有点儿像“燕赵文化”了,甚至于有点儿像现在的《燕赵文库》了,它就有了一个狭义的意思和一个广义的意思,狭义的意思很对,广义的意思也很对。

孙逢奇故居

孙奇逢雕像
所以我就有这样的一个考虑,从燕赵文化再到北学,我没有把燕赵文化和北学对立起来,它本来就是一起的,但是有角度的不同。北学是一个儒学概念、哲学概念,而燕赵文化应该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概念。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写这个文章的背景。我从1999年离开北大,在河南站了一下脚,就到湖南去了,到了湖南就做“湖湘学派”,做“湘楚文化”、“湘学”、“湖湘学”,也参与《湖湘文库》,于是我就有点儿像一个“双面间谍”。燕赵这边的事,燕赵文化的研讨会或者北学的研讨会我都参加,《燕赵文库》我也乐意跑过来参加,那边的《湖湘文库》我也参加,我也做《湘楚文明史》,就有点儿像一个“双面间谍”。
各个地域性的学派都是自娱自乐,谁都是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当然有好友请你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大家都是关心自己的家乡,全都是自己家乡最好,别人的我不管,但是我两边都跨,我两边都会想一想:原来做燕赵文化,它对不对?现在做湖湘文化,它对不对?我就会自然而然地在自己身上做一个比较。特别是这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湖南人开口闭口不是说毛泽东就是说曾国藩,这是他们的两块牌子,没这两块牌子日子就没法过。毛主席我们不敢说,说曾国藩,他在做直隶总督期间,有一篇给直隶学子的训词,湖南人很看重这个训词,而我们看这个训词的内容,好像是对燕赵文化特别是“燕赵悲歌”、“燕赵豪杰”的一种批评。那这里面我就要考虑是湖南对头还是河北对头?
还有我原来是读历史的,历史学界有一个说法叫做“满天星斗”,这个事我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不可能满天星斗,斗只能有一个,只能是满天星星,不能是满天星斗。所以我就说其实回到孙夏峰先生他本人的思路上来讲,他可能有一个想法,就是他一边要编《理学宗传》,一边要编《北学编》、《洛学编》。月印万川,理一分殊,“道”离不开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任何事情都是在时空里发生的,都离不开地域性,但是地域性又要体现出“道”的意思来。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道”悬挂在那里,没有那个东西,但是“道”代表者万事万物全体的、整体的一种关联。我们不能说只有地域性,没有万物的关联性。我们讨论地域性,不能离开“道”的意思。所以夏峰先生他们建立学统的时候,就同时具有这两方面的意思。我的文章就是在这两个方面做一点分析。“道”摆在什么位置上?地域摆在什么位置上?虽然我们是北学,虽然我们是做地域文化研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统一性的“道”。没有“满天星斗”,只有“万物皆载道”。天下只有一个“道”,任何地域的文化最后都应当祈向于这样一个“道”。

杨继盛祠堂
张京华教授在“儒学如何走入和影响时代”对话中发言说道:(录音整理廖叶)
儒学任何走入和影响现代”这个话题,对我而言是比较大的问题,我不太敢说。我好多年一直做古典,进入现代的都不太敢说。我还是结合我们会议的主题“北学”来说两句。

第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当然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时代,而我们是做文化的,那么我们肯定都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经济是个什么关系?我们在面对地方官员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1000万元修1公里的高速公路他愿意投资,20万元出一个学术著作他不出,他就是觉得你这个文化是没用的,文化没用。假使官员们每年给我们半公里的费用、0.1公里的费用,文化也就上去了。虽然是个小钱,可他不愿意做这个事儿。那么我就想,文化和经济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我自己把它解释为一种间接的关系。你不能说把孔子抬出来,把《论语》拿出来,直接到现代市场里去卖钱,如果要卖钱的话,《论语》这个文本打印出来也就一块钱的成本,但是如果没有孔子、没有《论语》,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国家它就不值钱。所以说文化是很值钱的,但是它不是直接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它是一种间接的关系。我就有这样一种间接论,是我自己的一个谬论。
那么我又说到北学,北学跟别的学派又有点儿不一样,北学讲实学日用,它是直接实践的。中国的很多学派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比较长远地对社会产生重要作用,而北学恰恰是直接地致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假使真的把北学家唤醒在我面前,我们跟他说:“你这个学问是北学”,他可能还不一定承认,就是说用一个“学”字说不定还不能限定住北学,因为它不完全是“学”,它是用“学”来致用,笼统说是一半学一半用。如果像今天这样,在学术研讨会上加以讨论,给它框定一个学科概念,说你是某某学,他可能不一定承认。严格来说可以说北学不是学,它就是一种致用的、一种直接的理论。所以北学这种精神也可以说更契合时代。
第二句对于北学我再加一点解释,就是如果我们碰到北学那些人物,特别是明末清初那些人,会遇到一个很可怜的现象,就是北学家想读书的时候他没书可读,因为北方本来就是经济不太发展,社会比较凋敝。明末清初的北学人物都发誓不再做官,明朝没有了,清朝的官是不能做的,然后家里就很穷,都是忍病停药的那种人,所以他没办法买书,看不到太多的书,北方也刻不起书。现在比如说我们读《资治通鉴》,会考虑读什么版本,读什么注本,读什么校本,他是连全本都读不到,只能读节本,《通鉴纲目》、《通鉴节要》什么的。他读五经,能读到胡广的《五经大全》就不错了。他们作诗,作诗可以不用太多的参考。他们写随笔,用零头碎纸抄抄写写的。王馀祐也称得上是著作等身了,主要内容是诗文、编写、抄写。南方的学者不同,像毛奇龄可以作《经义考》,江浙、安徽、福建的学者能看到大量的学术著作,从古本到晚近的都有,而北方学者看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北学在对古代学问的消化、理解上就限定为综合的、整全的,它不综合也不行。所以我有时候会想,北学是承接明学呢?还是承接宋学呢?其实它哪个都不承接,它哪个都知道一点点,哪个都知道得不详细,他也不往详细的讨论这个方向发展,他就是比较整全的、比较笼统的,这样提出一个符合它自己的实学实践的宗旨。学问无论粗细,最终都是用来指导实践的,它就抓住这一点。南方有一派学问,就是禅宗,不必读书,也可以顿悟。北学号称实学,不必多读书,只有能实践。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读《颜习斋年谱》,在康熙十八年颜元四十五岁的时候,这天,安州有个陈天锡来找他谈学问,问他儒学应该是个什么样子?颜元就跟他说,我帮你虚拟两间书堂:一间书堂里坐的是孔子,弟子在旁边侍立,干什么呢?讲礼,讲兵学,讲礼乐射御,士农工商,墙上挂的是弓箭,门口停的是战车,排练文舞、武舞。还有一个书堂坐的是程子,像泥塑一样静坐不动,弟子们在旁边或者捏着笔著述,或者执着本子呻吟诵读,或者干脆静坐打坐,桌上放着什么呢?放着字画,要不就放点梨枣,放点水果什么的。颜元说你看这两种儒家一样吗?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照颜元的意思,不只说王学,就连程朱理学都跨越过去了,直接接到孔子上去了,然后从孔子再往上走,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他们的思想根基其实是在“六府三事”上面。
“六府三事”出于《书经》,讲的是唐虞三代的政治,后来《左传》里面也有发挥。“六府”是水、火、金、木、土、谷,都是我们说的经济部门,工业、农业部门。“三事”是正德、利用、厚生,这样三个原则。北学讲的是这些东西,所以他们的思想,表面上是直接在当代社会里致用,实际上这个根基是彻底地复古。这里我就举一句刁包刁紫峰的话,他有一句特别极端的话就是“作时文不作古文者,文不文;作时人不作古人者,人不人”。要写文章,那就只能是三代的文章,不然这文章就不是文章;要做人就得做三代的人,要不然这人他就不是人。说得很极端,但是也很能突出他的观点,就是复古,所以北学是超越了明学和宋学,复古到三代。这一点很像是张横渠,但是比张横渠还要彻底。
那么说到这儿,我们要说回来。说到“复古”这个问题,其实历史上很多学术思潮、学术进步都是从复古开始的,谁要想复古都是不可能的,复古的结果其实都是创新,古代的东西不可能百分百地恢复,复古的结果一定是一个新的东西、新的思想。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典例,欧洲回到古希腊了吗?没有,它搞出来工业革命了。所以梁任公后来就有一个观点,说复古就是创新,复古就是解放。从这方面来讲,北学的复古也可以给今天新时代的创新提供一个借鉴。
文化比较忌讳的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所以我就结合北学来做一点发挥。到时间了,谢谢大家!

孙奇逢浮雕
主持人梁枢:您讲的这个复古,应该是什么?北学就是表达出一种形式上的复古,实质是要回到西周,是这个意思吗?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以你讲这个儒家文化,它其实是成长的。成长就是比如说一个小孩,三个月高半个头,高出来的这半个头它是新的吗?你能从这半个头中说这是新长出来的部分,真假的部分你能分出来吗?成长一定是一个有机的改变,它一定是新旧杂糅在一起。
张京华:真假的用语是太简单了,“假的”应该是指一种在当年是合理的、在后来却不合时宜的时代变迁,就是指一种不合理、不适宜。一个人七岁,七岁的时候他做一个七岁的人就是对的。后来他长到十二岁,十二岁的时候他做一个十二岁的人也是对的。因为儒家讲究“时义”,“时乎时”,“时为大”,其实“中庸”也就是“时中”。“假的”是说在“时中”的标准下,它是时空错位的。


